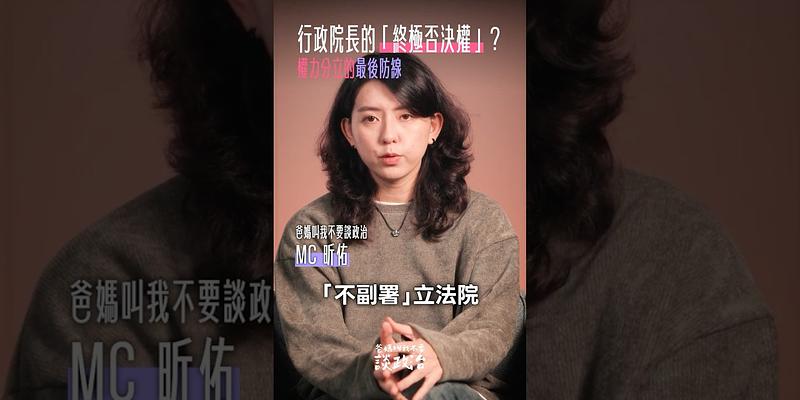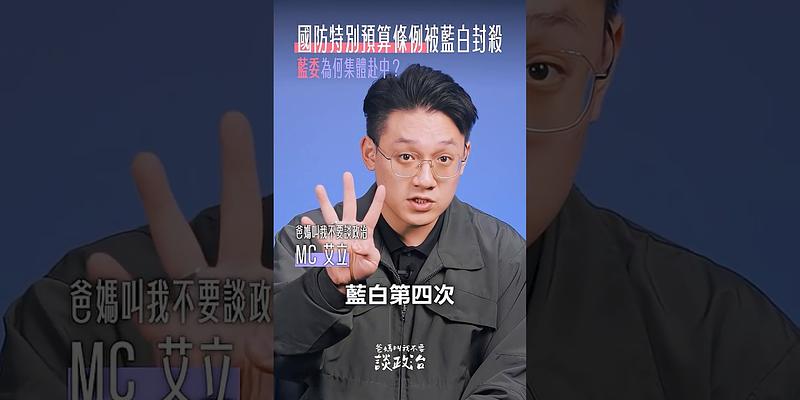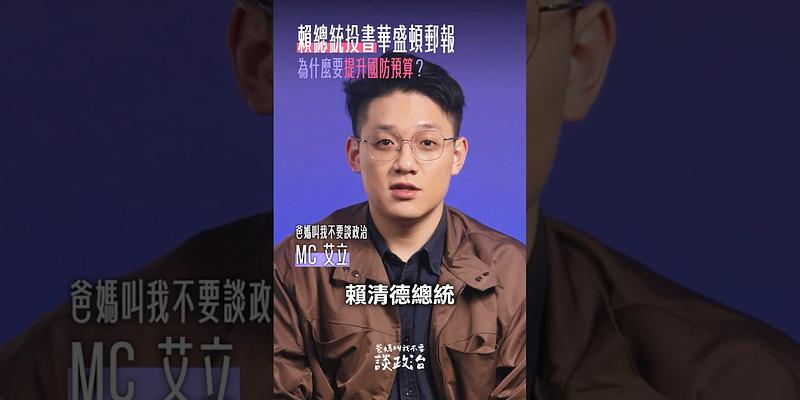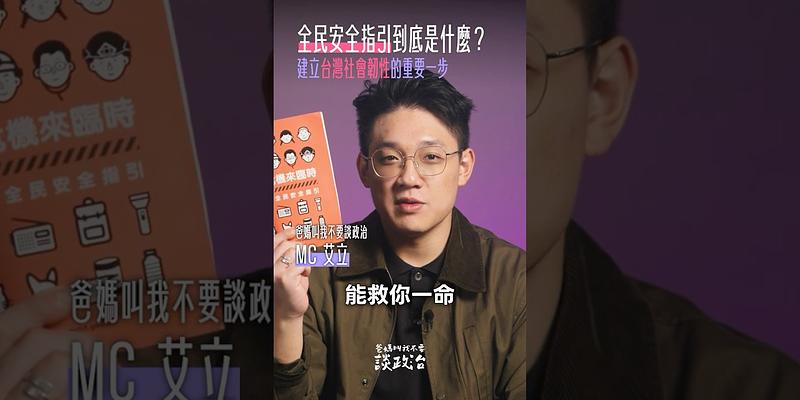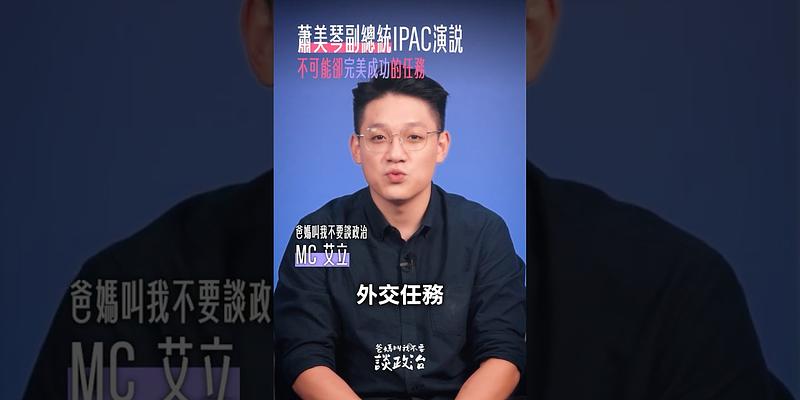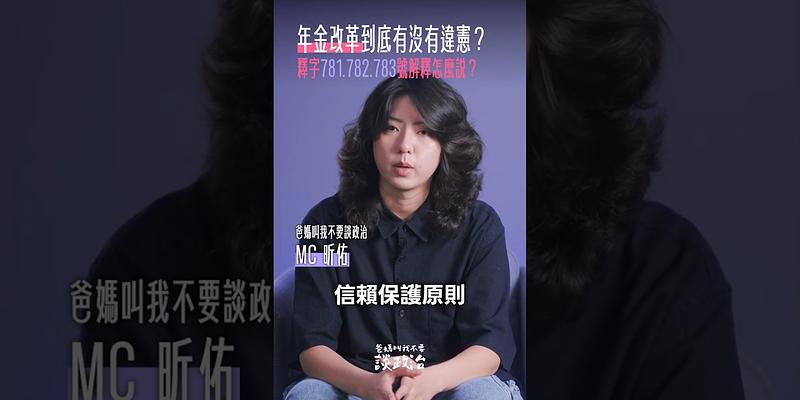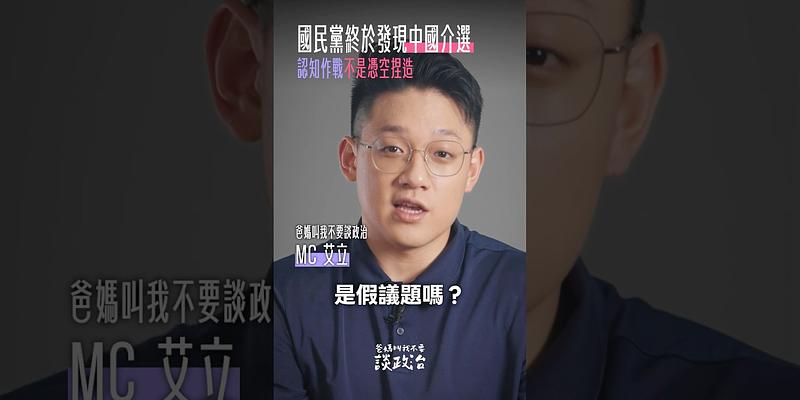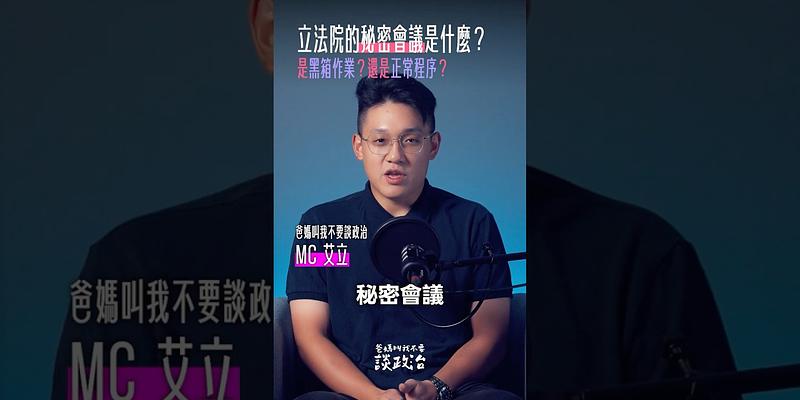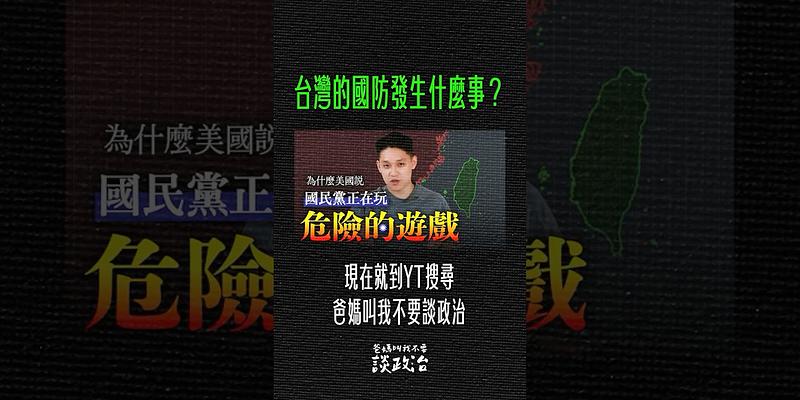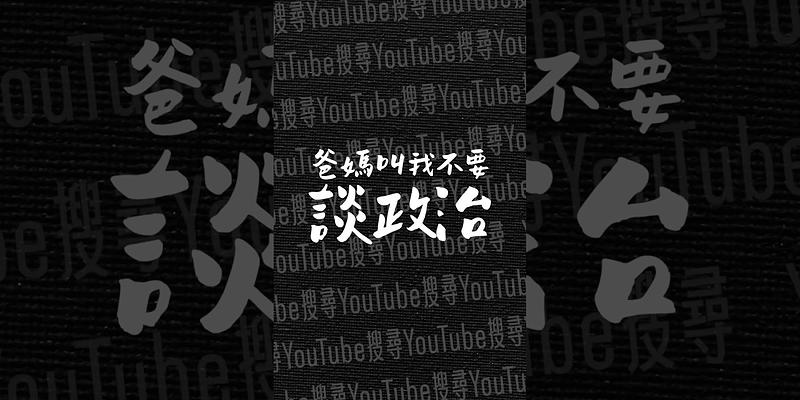論司法院定位
新境界文教基金會
壹、問題背景
司法院定位是我國司法改革的核心問題, 1997 年 5 月 8 日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台北律師公會、台灣法學會及法官協會等法界重要團體共同拜會當時的李登輝總統,請求總統召開全國司改會議。此項請求雖經李總統允諾,並交由司法院籌辦,但是準備過程中,因為民間團體認為司法院預設立場,缺乏改革誠意,拒絕接受而無法進行,並於同年 10 月 19 日聯合律師、法官、檢察官、法學教授、弱勢團體人士、及社會各界人士等 3000 餘人舉辦「為司法改革而走」大遊行,引起社會極大矚目[1]。其後,由翁岳生大法官並任司法院院長後,方有進展。
除前述會議結論外,司法院也針對本身的地位於 2001 年 10 月 5 日所作成的釋字第 530 號解釋中指出,現行司法院組織法規定,在司法院之下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導致司法院除審理解釋憲法及統一解釋法令案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之大法官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行政機關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行政機關分離。該號解釋更要求,為期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行政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
因應此號解釋,司法院曾向立法院提出相關組織法修法草案,卻因為國民黨主導的杯葛與阻礙,以及屆期不連續,導致至今為止司法院定位改革並未成實現。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更是走回頭路。司法院以評估 1999 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結論中有關司法院審判機關化的定位改革推動成效的名義,於 2011 年成立「司法院定位改革成效評估委員會」。形式上是重新評估司法院定位改革成效,釐清司法院審判機關化及體制金字塔化等改革理念背後之問題,以及是否仍有 1999 年全國司改會議所未提出之其他隱藏性議題,實質上是推翻前述全國司改會議結論,此由評估總結論:「88 年全國司改會議做成司法院應朝審判機關化改制之結論,不宜繼續推動,但有必要審酌改制思維,在現制下儘可能落實其理念」即可明白。由司法院召開委員會就將當年具備廣泛代表性的結論擱置及另起爐灶,完全顯示司法院的保守性與反民主性,也凸顯出目前的司法院根本不遵守釋字第 530 號解釋,已經明顯違憲。
貳、主要問題
關於司法院定位未能落實的主要原因有下列幾項,也是未來深化司法改革必須處理的問題:
1、各最高審判機關的反對。
現行司法院模式是訓政時期「黨治形態」的遺緒,司法必須對黨負責。現行憲法實施後,司法院主要還是負責司法行政任務,審判職務是由所轄的普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執行,因此才有釋字第530號解釋。前述會議結論有關司法院定位無法貫徹的主要原因就是各最高審判機關的反對。無論是一元單軌或一元多軌都將使各最高審判機關裁撤,喪失原來的「最高性」。
2、擔心憲法解釋功能的喪失。
另外,亦有認為一元單軌之後原來司法院解釋憲法的功能將喪失,以13位至15位大法官要掌理所謂的審判事務,則大量的民、刑事及行政訴訟勢必耗盡大法官的大部分時間與精力,原來得以集中於憲法解釋的功能將逐漸減弱化,反而不利於憲政發展。
3、違憲審查制度改革的爭議。
若是司法院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般成為最高審判機關,肩負沉重之審判職務,則違憲審查制度是否也應從現行的集中審查制,改為美國式的分散審查制?此項問題在前述司改會議中並未討論,所以前述改革成效評估委員會作出憲法解釋繼續朝法庭化及裁判化方向改革的結論,此點是未來定位司法院的重要思考點。
4、司法院要成為最高審判機關化,還是成為憲法法院仍有爭論。
司法院最高審判機關化是否只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模式?還是德奧的憲法法院模式?這是重新檢視前述司改會議必須思考的問題。兩者都有違憲審查制度但方式不同,在思考司法院定位時必須同時思考如何設計此項保障人權的制度。
參、主張
司法院定位問題必須穩健處理,我們主張:
- 司法院應朝審判機關化方向改革,至於是採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模式或德國憲法法院模式,可以再討論。
- 重新召開全國司改會議,檢視 1999 年之後未貫徹執行之司法改革問題,並重新省思司法院定位等核心的司法制度問題。不能僅以所謂評估委員會方式就推翻原來的結論。
- 擴大人民參與。司法改革是人民的司法改革,不是法律菁英的司法改革。1999 年全國司改會議是法學菁英會議,欠缺公民社會的參與,導致人民對於司法改革欠缺資訊及漠不關心。
- 修改司法院組織法、法院組織法及其他相關配套法律。
- 修正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將司法院解釋憲法方式以裁判方式進行。